让父的坟墓向北方
来源:隆回民间文艺公众号撰稿:周玉清时间:2017-07-14点击:次
1992年12月18日下午,我在北京雅宝路的空军招待所大礼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。刚把有关文秘方面的一应事宜处理完,便接到大会秘书处转来的电话通知,让我马上回单位。匆匆回到我当时的单位中央办公厅,一份老家来的电报摆在我面前:“父去世,速回”。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,把我惊呆了,一时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。父亲除了眼疾,身体一直很健康。当时他已年满八十,仍舍不得丢下自家的责任田。之前,我每次劝他离田上岸颐养天年时,他总是说,我还能动,田还得作,你现在工资低,孩子又小,我和你娘不要给你增添负担。他满八十后,我的劝说有了些效果,他终于答应把责任田另租他人,争取春节后到北京来看看过去皇帝住的地方。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?
当时,坐飞机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,我从北京坐火车、转汽车、再步行,日夜兼程赶到老家时,已是父亲辞世三天后的凌晨。父亲的灵柩摆在堂屋中央,清冷的夜空里传来守灵的家里人和众多亲友乡邻们不约而同的啕哭。拖着注满沉铅一样的步子进门,我丢下行李,在父亲的灵柩前拜了三拜,想到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与我们天各一方,我猛地伏在父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:“儿子不孝,回来迟了!……”
父亲的辞世是一个意外。那天,父亲随着村里赶集的大队人马去15里外的石江镇看我姐姐。他本可在姐姐家住下的,下午四点左右,父亲执意随村里大队伍回家。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,父亲在天色黑时分走到了离家只有300米左右的地方时,他不顾自己的眼疾,绕道去看自留地里种的蔬菜。当时,村里同行的人也没在意,而母亲却以为父亲住在姐姐家里不回来了。父亲辞世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。据后分析,他是从菜地旁很窄的田埂上栽下去的,在野外寒冷的冬夜里冻饿13个小时而无人知晓,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。父亲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里的山梁,最后倒在自己眷恋的土地上。
在我还没有赶回老家之前,村里已经为父亲选好了墓地。墓地选在村后坐南朝北的山腰。山很高,墓地的位置也很高。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,参加送葬的人数也很多,打着幡旗、穿着白衣、头上扎着白布的送葬队伍,从田间到山下再到山腰,逶迤连绵,一眼望不到头。当各项应搞仪式结束之后,送葬的乡邻陆续离去。我呆呆地站在父亲的坟头,向北望去,群山起伏,云蒸雾遮,苍茫无涯。我百感交集,悲从心起:那数千里之外的北京,是他唯一儿子工作的地方。虽然父亲去北京看“皇宫”的意愿没有实现,但我仿佛看到父亲的慈爱依旧,威严犹在。如果世间真有灵魂,那父亲的灵魂也一定在守望着儿子栖居的北方。
贫穷和苦难一直伴随着父亲。父亲成年后,大多岁月是靠当长工、打短工度过的,为了“躲壮丁”,他去了一百多里路远的瑶族山寨谋生,眼睛因深山老林里瘴毒之气侵袭发炎,得不到及时医治,落下眼疾而半失明,但在犁田、耙田、挖土等粗活上仍是一把好手,在村里熟悉的山间地头上行走也很自如。终究因眼睛有疾而干不好细活,比如锄草,错把麦苗当杂草除掉的事常有发生。为了节省布鞋,无论上山还是下田,他都是赤脚。有一次,年幼的我随父亲上山砍柴,一根很尖的柴兜刺穿了他的脚板,他的脚血肉模糊,我慌忙飞跑着回村里喊人把他抬回去。家里没钱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为他治伤,只得让邻村的郎中敷上草药,十来天后,他又挣扎着拄着拐杖上山挖土。
我的两个哥哥在解放前就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,我五岁那年,父母给我“看八字”,说我前世欠债也将生命不保,而且很有可能在“水”字上出事。刚好我家门前有两口水塘。父母一听急了,赶忙恳求“八字先生”想办法,先生回答:要想保命,唯有“斩楼顶”。“斩楼顶”是流传于湘中南地区梅山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仪式,也是当时乡下花费最昂贵的一项民间“法事”活动,需要请“师公”搞一个通宵,花费六担稻谷(约800斤)。当时的水稻都是单季、高杆,亩产只有300斤左右,有时碰上大风,稻杆倒伏,便是颗粒无收。六担稻谷是我家两年的收成,用六担谷子做“法事”,预示着我家要数年背债,家里人只能靠土里的红薯过日子。父亲“叭哒”着长筒烟袋,许久没有吱声,最后把长杆烟筒往地上一咂,对我妈妈说:借帐也要办“斩楼顶”。
“斩楼顶”的“法事”活动在冬夜里通宵达旦地进行,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观看,挤满了我家本来很小的堂屋。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大约两小时的“程序”:“师公”脱光上衣,用磨得锋利的木匠斧头砍胸脯,围着摆满贡品的小长桌边砍边唱书文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那晚“师公”唱的是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。“师公”砍胸脯的力度掌握得很巧妙,看着重重落下来的斧头,在胸脯上只是轻划一下,当表皮的毛细血管渗出血后,“师公”就用不大的陶制杯子刮一下,让渗出的血液流进杯里,又继续边砍边唱。待到杯子里的血液将满时,“师公”让我跪在神龛前,把陶瓷杯里的血喝下去,求上苍保佑我长命富贵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喝血,很不情愿,当看到父亲一脸的严厉时,我只得照办。咬紧牙关喝了下去后,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,似乎独生子的性命从此有了保障。
极度的贫穷使父亲没有能力送儿女上学。1952年,离我家三华里远的花冲村新办了一所初小,每期学费5角钱。在校长的一再动员下,父亲答应让6岁的我去读书,但不答应姐姐上学。家里缺劳动力,姐姐每天必须帮着父亲干农活,还要负责打猪草。如果我读书,原来由我看牛的任务也要由姐姐承担。姐姐当时已经14岁,再不上学就太迟了。校长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扫盲任务,也为了增加生源,反复动员父亲让姐姐读书,答应免除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,并且可以牵牛上学。就这样,姐姐上课时把牛拴在学校旁的树林里,带着我一同上了小学一年级。两年后,姐姐还是辍学了,因为穷啊。
1961年,我在隆回十中初中毕业,当时隆回县有十几所中学,但是只有一中和二中每年各招两个高中班,考上高中就像是中了“状元”。也许是我临场发挥得好,我成了那年隆回十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人。消息传出,引起了周围几个公社的轰动,村里的乡亲们对我更是一片赞扬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父亲却不让我读——家里交不起每学期十五块钱的学杂费和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。在我的哭闹和村里人的劝说下,父亲下决心卖猪,卖掉那头能够包揽全家一年油盐钱的大肥猪。这头猪在集上卖了十八块钱,勉强凑足了入学时起码的费用。我家是农村户口,上学的粮食和菜必须自带,学校负责蒸饭加工,每餐供应一个菜汤,但学生每月要交三块钱的搭伙费。隆回一中在离我家55里的县城,我每个星期必须回家挑粮食,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离校,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到家。星期天中午后,挑着够一个星期吃的粮食——大多数为红薯或红薯干,带着用荷叶包着的辣椒粉赶往学校。去县城的漫漫山路上,每个星期都会出现我挑着沉重担子艰难跋涉的身影。入学第二个月,我开始交不起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了。每个星期必须带一元钱交学校,否则就会被“停餐”。父亲显得很无奈,到哪里去筹这一元钱呢?我缠着向他要,吵得他烦了,用长杆烟锅驱赶我。最后,总是妈妈挨家挨户去借,或者卖几个鸡蛋几斤大米,才凑足这要命的一元钱。
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,家里实在没办法供我读书了,眼看就要辍学,乡邻们都来劝父亲:你家孩子会读书,停学太可惜了。乡邻们也是爱莫能助,帮不上忙。父亲叭哒叭哒着那根长杆烟袋,沉默了许久。而我,几乎都绝望了。出人意料的是,父亲有天突然不容分说地对母亲说:把咱们的棺材料卖了。
那两副上等的杉木棺材料一共18根,是1958年那个大炼钢铁而疯狂砍树的年代,父亲用100多担杂柴换取的指标,找人帮忙从深山老林给拾回来的,以后很难有这么粗大的树料了。这两副棺材料,不仅凝聚着父亲的血汗,也是父母百年后的寄托。由于出手急,两副棺材料只卖了150块钱。靠着这150块钱,我读完了三年高中,1964年高考时,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,因为师范类院校不用交任何费用。
大学毕业后,我走进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舞台,开始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漂泊之旅。几十年来,我换了许多岗位,也到过山南海北、国内国外很多地方,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来报答父母的恩德。身在异乡,常常梦见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身影,时时感触着如大山一样厚重的父爱。
光阴荏苒,父亲去世已经十八年了,但我对父亲的怀念却日益深重。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嫩绿的日子,那些夹带着苦涩的快乐,也许会随时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褪,但父亲的大爱和恩情我将永远铭记。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从北京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祭奠,每一次,我默默地念叨:愿父亲在天国幸福……每一次,当我转身离去时,总是感觉到,我的背脊上依旧有两道苍老而又温暖的目光。
我相信,父亲一直在身后看着,一直在望着遥远的北方,那是他儿子至今仍栖居的异乡。


图为周玉清投资为家乡南岳庙塘现村修建的清风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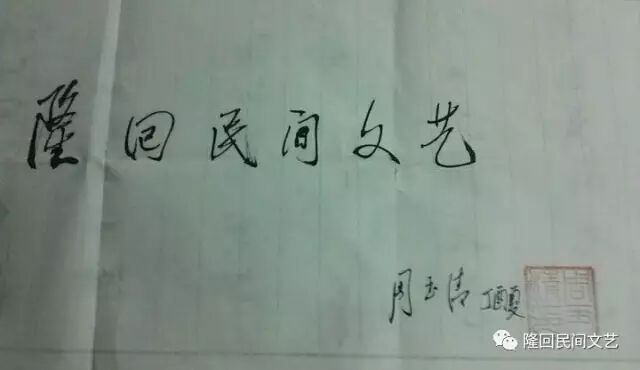
周玉清老前辈亲自为《隆回民间文艺》题书
作者简介:

周玉清,男,1946年7月出生,隆回南岳庙人,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,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、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)
(版权声明:隆回民间文艺公众号授权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网站刊发,编辑曾振华)
当时,坐飞机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,我从北京坐火车、转汽车、再步行,日夜兼程赶到老家时,已是父亲辞世三天后的凌晨。父亲的灵柩摆在堂屋中央,清冷的夜空里传来守灵的家里人和众多亲友乡邻们不约而同的啕哭。拖着注满沉铅一样的步子进门,我丢下行李,在父亲的灵柩前拜了三拜,想到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与我们天各一方,我猛地伏在父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:“儿子不孝,回来迟了!……”
父亲的辞世是一个意外。那天,父亲随着村里赶集的大队人马去15里外的石江镇看我姐姐。他本可在姐姐家住下的,下午四点左右,父亲执意随村里大队伍回家。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,父亲在天色黑时分走到了离家只有300米左右的地方时,他不顾自己的眼疾,绕道去看自留地里种的蔬菜。当时,村里同行的人也没在意,而母亲却以为父亲住在姐姐家里不回来了。父亲辞世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。据后分析,他是从菜地旁很窄的田埂上栽下去的,在野外寒冷的冬夜里冻饿13个小时而无人知晓,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。父亲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里的山梁,最后倒在自己眷恋的土地上。
在我还没有赶回老家之前,村里已经为父亲选好了墓地。墓地选在村后坐南朝北的山腰。山很高,墓地的位置也很高。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,参加送葬的人数也很多,打着幡旗、穿着白衣、头上扎着白布的送葬队伍,从田间到山下再到山腰,逶迤连绵,一眼望不到头。当各项应搞仪式结束之后,送葬的乡邻陆续离去。我呆呆地站在父亲的坟头,向北望去,群山起伏,云蒸雾遮,苍茫无涯。我百感交集,悲从心起:那数千里之外的北京,是他唯一儿子工作的地方。虽然父亲去北京看“皇宫”的意愿没有实现,但我仿佛看到父亲的慈爱依旧,威严犹在。如果世间真有灵魂,那父亲的灵魂也一定在守望着儿子栖居的北方。
贫穷和苦难一直伴随着父亲。父亲成年后,大多岁月是靠当长工、打短工度过的,为了“躲壮丁”,他去了一百多里路远的瑶族山寨谋生,眼睛因深山老林里瘴毒之气侵袭发炎,得不到及时医治,落下眼疾而半失明,但在犁田、耙田、挖土等粗活上仍是一把好手,在村里熟悉的山间地头上行走也很自如。终究因眼睛有疾而干不好细活,比如锄草,错把麦苗当杂草除掉的事常有发生。为了节省布鞋,无论上山还是下田,他都是赤脚。有一次,年幼的我随父亲上山砍柴,一根很尖的柴兜刺穿了他的脚板,他的脚血肉模糊,我慌忙飞跑着回村里喊人把他抬回去。家里没钱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为他治伤,只得让邻村的郎中敷上草药,十来天后,他又挣扎着拄着拐杖上山挖土。
我的两个哥哥在解放前就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,我五岁那年,父母给我“看八字”,说我前世欠债也将生命不保,而且很有可能在“水”字上出事。刚好我家门前有两口水塘。父母一听急了,赶忙恳求“八字先生”想办法,先生回答:要想保命,唯有“斩楼顶”。“斩楼顶”是流传于湘中南地区梅山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仪式,也是当时乡下花费最昂贵的一项民间“法事”活动,需要请“师公”搞一个通宵,花费六担稻谷(约800斤)。当时的水稻都是单季、高杆,亩产只有300斤左右,有时碰上大风,稻杆倒伏,便是颗粒无收。六担稻谷是我家两年的收成,用六担谷子做“法事”,预示着我家要数年背债,家里人只能靠土里的红薯过日子。父亲“叭哒”着长筒烟袋,许久没有吱声,最后把长杆烟筒往地上一咂,对我妈妈说:借帐也要办“斩楼顶”。
“斩楼顶”的“法事”活动在冬夜里通宵达旦地进行,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观看,挤满了我家本来很小的堂屋。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大约两小时的“程序”:“师公”脱光上衣,用磨得锋利的木匠斧头砍胸脯,围着摆满贡品的小长桌边砍边唱书文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那晚“师公”唱的是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。“师公”砍胸脯的力度掌握得很巧妙,看着重重落下来的斧头,在胸脯上只是轻划一下,当表皮的毛细血管渗出血后,“师公”就用不大的陶制杯子刮一下,让渗出的血液流进杯里,又继续边砍边唱。待到杯子里的血液将满时,“师公”让我跪在神龛前,把陶瓷杯里的血喝下去,求上苍保佑我长命富贵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喝血,很不情愿,当看到父亲一脸的严厉时,我只得照办。咬紧牙关喝了下去后,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,似乎独生子的性命从此有了保障。
极度的贫穷使父亲没有能力送儿女上学。1952年,离我家三华里远的花冲村新办了一所初小,每期学费5角钱。在校长的一再动员下,父亲答应让6岁的我去读书,但不答应姐姐上学。家里缺劳动力,姐姐每天必须帮着父亲干农活,还要负责打猪草。如果我读书,原来由我看牛的任务也要由姐姐承担。姐姐当时已经14岁,再不上学就太迟了。校长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扫盲任务,也为了增加生源,反复动员父亲让姐姐读书,答应免除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,并且可以牵牛上学。就这样,姐姐上课时把牛拴在学校旁的树林里,带着我一同上了小学一年级。两年后,姐姐还是辍学了,因为穷啊。
1961年,我在隆回十中初中毕业,当时隆回县有十几所中学,但是只有一中和二中每年各招两个高中班,考上高中就像是中了“状元”。也许是我临场发挥得好,我成了那年隆回十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人。消息传出,引起了周围几个公社的轰动,村里的乡亲们对我更是一片赞扬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父亲却不让我读——家里交不起每学期十五块钱的学杂费和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。在我的哭闹和村里人的劝说下,父亲下决心卖猪,卖掉那头能够包揽全家一年油盐钱的大肥猪。这头猪在集上卖了十八块钱,勉强凑足了入学时起码的费用。我家是农村户口,上学的粮食和菜必须自带,学校负责蒸饭加工,每餐供应一个菜汤,但学生每月要交三块钱的搭伙费。隆回一中在离我家55里的县城,我每个星期必须回家挑粮食,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离校,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到家。星期天中午后,挑着够一个星期吃的粮食——大多数为红薯或红薯干,带着用荷叶包着的辣椒粉赶往学校。去县城的漫漫山路上,每个星期都会出现我挑着沉重担子艰难跋涉的身影。入学第二个月,我开始交不起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了。每个星期必须带一元钱交学校,否则就会被“停餐”。父亲显得很无奈,到哪里去筹这一元钱呢?我缠着向他要,吵得他烦了,用长杆烟锅驱赶我。最后,总是妈妈挨家挨户去借,或者卖几个鸡蛋几斤大米,才凑足这要命的一元钱。
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,家里实在没办法供我读书了,眼看就要辍学,乡邻们都来劝父亲:你家孩子会读书,停学太可惜了。乡邻们也是爱莫能助,帮不上忙。父亲叭哒叭哒着那根长杆烟袋,沉默了许久。而我,几乎都绝望了。出人意料的是,父亲有天突然不容分说地对母亲说:把咱们的棺材料卖了。
那两副上等的杉木棺材料一共18根,是1958年那个大炼钢铁而疯狂砍树的年代,父亲用100多担杂柴换取的指标,找人帮忙从深山老林给拾回来的,以后很难有这么粗大的树料了。这两副棺材料,不仅凝聚着父亲的血汗,也是父母百年后的寄托。由于出手急,两副棺材料只卖了150块钱。靠着这150块钱,我读完了三年高中,1964年高考时,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,因为师范类院校不用交任何费用。
大学毕业后,我走进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舞台,开始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漂泊之旅。几十年来,我换了许多岗位,也到过山南海北、国内国外很多地方,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来报答父母的恩德。身在异乡,常常梦见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身影,时时感触着如大山一样厚重的父爱。
光阴荏苒,父亲去世已经十八年了,但我对父亲的怀念却日益深重。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嫩绿的日子,那些夹带着苦涩的快乐,也许会随时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褪,但父亲的大爱和恩情我将永远铭记。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从北京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祭奠,每一次,我默默地念叨:愿父亲在天国幸福……每一次,当我转身离去时,总是感觉到,我的背脊上依旧有两道苍老而又温暖的目光。
我相信,父亲一直在身后看着,一直在望着遥远的北方,那是他儿子至今仍栖居的异乡。


图为周玉清投资为家乡南岳庙塘现村修建的清风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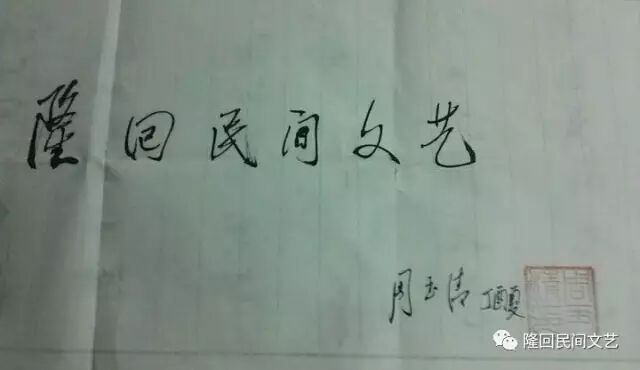
周玉清老前辈亲自为《隆回民间文艺》题书
作者简介:

周玉清,男,1946年7月出生,隆回南岳庙人,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,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、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)
(版权声明:隆回民间文艺公众号授权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网站刊发,编辑曾振华)
- 上一篇:寻找父亲的足迹
- 下一篇:君之道国学弟子参学洞口高沙曾子书院
